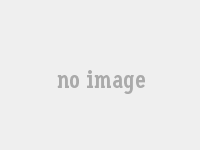民国二十三年的秋夜,月凉如水,打湿了津门西郊的荒草。我攥着半块啃剩的驴打滚,跟在老周身后深一脚浅一脚地走,耳边尽是虫鸣与远处火车的闷哼。老周是城南“福顺祥”的账房先生,前几日忽然愁眉不展,问起才知他那独子小周,放着安稳的商铺伙计不当,非要往西郊的“恒通汽配厂”钻。“都说那厂子挣钱,可我总放心不下,”老周的烟袋锅在黑暗中一亮一灭,“你常写那些奇闻,胆子大,陪我去瞧瞧究竟,也弄明白汽配厂工资待遇怎么样。”
恒通汽配厂的围墙比寻常商号高出半截,墙头插着碎玻璃,在月光下泛着冷光。我们绕到侧门,正撞见一个穿粗布工装的后生蹲在石阶上啃馒头,袖口沾着黑油,脸上却带着笑意。老周上前递了袋烟,后生倒也爽快,三两口咽下馒头便开了口。他叫二柱,是厂里的学徒,来这儿刚满半年。“起初家里也拦着,说打铁都比这体面,”二柱挠了挠头,“可我叔在这儿当老师傅,说这儿规矩虽严,钱却实打实。我现在是学徒,管吃管住,一个月还能拿三块大洋,比在杂货铺当学徒强多了。等出了师,跟着师傅做精密的轴承活儿,一个月少说七八块,要是赶上年终订单多,还能分红利。”他说着从怀里摸出个油布包,里面整整齐齐叠着几块银元,“我娘说,照这光景,明年就能给我攒够彩礼钱。”
正说着,侧门“吱呀”一声开了,一个面色蜡黄的中年汉子走了出来,咳嗽着扶住墙。二柱见了他,连忙起身问好,称他为“李师傅”。李师傅瞥见我们,眼神有些躲闪,老周忙上前说明来意,问起汽配厂工资待遇怎么样。李师傅叹口气,找了个避风的墙角坐下,缓缓说道:“我在这儿做了五年,专做发动机活塞,手艺不算顶尖,但也差不到哪儿去。正常月份,基本工资六块,加上计件的提成,能拿到十块左右。可这活儿伤身子,机油味闻多了,肺里总像堵着东西。厂里管医药费,但要是请长假,当月的全勤奖就没了。前阵子我媳妇生娃,我请了半个月假,上个月只拿了五块钱。”他从口袋里摸出个小药瓶,倒出几粒黑色的药丸吞下,“不过话说回来,比起乡下种地,这儿的钱还是好挣些。我家小子在城里读书,学费杂费全靠我这点工资撑着。”
我们正听得入神,忽然听见厂里传来一阵喧哗,二柱脸色一变,说怕是工头查岗了,催着我们赶紧离开。老周还想再问,却被二柱推着往暗处躲。躲在树丛后,只见几个穿黑褂子的工头举着灯笼走过,嘴里骂骂咧咧地说着“怠工扣钱”之类的话。等工头走远,二柱才低声说:“厂里规矩严,上班不许偷懒,要是被抓到迟到早退,一次就扣一块大洋。但要是肯加班,加班费给得足,晚上加一个时辰,算两个时辰的工钱。上个月赶一批给洋行的订单,我连着加了十天班,拿了十二块大洋,是我长这么大拿得最多的一次。”他说着,脸上又露出了兴奋的神色,“就是累,每天下了班,倒头就能睡着。”
往回走的路上,老周的烟袋锅一直没停。快到城门口时,忽然遇见一个挑着担子的货郎,担子上插着些针头线脑。货郎见我们从西郊方向来,笑着说:“二位是去恒通汽配厂了?这厂子近来名气大得很,不少乡下人都往那儿跑。前几天我给厂里送肥皂,听见几个女工在说工资的事。那些做装配活儿的女工,一个月也能拿四五块大洋,比纺纱厂的女工强多了。就是活儿细,稍微出点错就得扣钱。有个女工把螺丝拧错了位置,当月就扣了两块,哭得不行。”货郎顿了顿,又说:“不过厂里管饭,顿顿有荤腥,住宿也干净,比很多厂子都强。”
回到老周家,他把小周叫到跟前,把我们听到的一五一十说了。小周听后,反倒更坚定了去厂里的念头:“爹,我打听清楚了,厂里的学徒出徒后,要是能进技术部,学做汽车零件的设计,工资能翻两倍。我在商铺学不到这些真本事,去厂里既能挣钱,又能学手艺,多好。”老周看着儿子眼里的光,终究没再反对,只是反复叮嘱他要注意身体,别太拼命。
半个月后,小周正式进了恒通汽配厂。第一个月发薪时,他攥着三块大洋跑回家里,兴奋地给老周讲厂里的事。他说李师傅帮他改了好几次活儿,还教他辨认零件的好坏;说二柱带他熟悉了厂里的各个工序,告诉他哪个工种挣钱多,哪个工种相对轻松;说厂里的食堂饭菜确实不错,中午有红烧肉,晚上有鸡蛋汤。老周看着儿子脸上的朝气,终于放下了心。
后来我又去过西郊几次,每次都能看到恒通汽配厂的门口挤满了找活儿的人。有一次遇见二柱,他已经出徒了,穿着崭新的工装,手里拿着图纸,说自己现在专门做进口汽车的配件,一个月能拿十五块大洋,还娶了媳妇,就在厂附近租了房子。李师傅的身体也好了些,厂里新添了通风设备,他说现在干活儿舒服多了,上个月拿了十三块大洋,给儿子买了新的书包和笔墨。
津门的冬天来得早,寒风卷着雪花落在汽配厂的屋顶上。厂里的灯火彻夜通明,机器的轰鸣声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清晰。那些在厂里劳作的人们,或许也曾迷茫过、犹豫过,但当他们拿到用汗水换来的工钱时,脸上总会露出踏实的笑容。汽配厂工资待遇怎么样?不同的人或许有不同的答案,但对于那些靠着双手谋生的人来说,这里的每一块银元,都承载着他们对生活的希望与期盼。就像老周常说的,只要钱来得干净,活儿做得踏实,日子就一定能越过越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