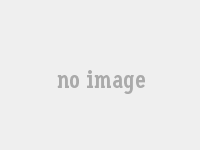1992 年夏天,我带着伦敦总部的任命抵达新加坡,出任巴林期货公司总经理。彼时的巴林银行正值第 229 个年头,伊丽莎白女王的签名还印在它的客户名录上,没人能料到这家曾资助过路易斯安纳购地案的金融巨头,会在三年后栽在我手里。清算部同事利塞尔敲下键盘时,或许只是觉得 “88888” 这个五位数账号讨个吉利,却没意识到它会成为埋葬百年基业的坟墓 —— 这是伦敦总部为简化小错误处理流程临时设立的账户,不久后被搁置却未注销,成了我日后操作的关键缺口。
最初的失足始于手下交易员金・王的失误。这位入职仅一周的新人将富士银行买进 20 手日经指数期货的指令错判为卖出,当晚清算时显示亏损 2 万英镑。按规定应立即上报伦敦,但看着屏幕上跳动的数字,我突然想到了那个被遗忘的 “88888” 账户。将 40 手空头合约转入该账户的瞬间,我第一次尝到了隐瞒的滋味,却没察觉这步棋已将自己推向深渊。几天后日经指数上涨 200 点,亏损扩大至 6 万英镑,相当于我全年的薪水,上报的念头彻底被恐惧压了下去。
好友乔治的失误让窟窿进一步扩大。离婚后的他状态低迷,将我指令卖出的 100 份九月期货合约误作多头买入,800 万英镑的错误交易几乎要击穿隐瞒的底线。我再次动用 “88888” 账户兜底,同时开始通过跨式部位交易赚取期权权利金,试图填补亏空。幸运的是,1993 年的日经指数相对稳定,到 7 月时账户竟从 600 万英镑亏损转为略有盈余,这让我获得了 10 万英镑年终奖,也让总部对新加坡分行的 “业绩” 更加信任。这种短暂的成功像麻醉剂,让我忽略了期货交易的杠杆风险,更忘了自己身兼交易与清算两职本就是制度大忌。
1994 年成了失控的开端。为争夺大客户波尼弗伊,连续几天的市场暴涨让故障频发的清算系统陷入瘫痪,等人工厘清账目时,单日损失已达 170 万美元。我不得不加大投机力度,将赌注押在日经 225 指数期货上,幻想着靠市场反转一次性翻盘。此时 “88888” 账户的亏损已累积到 5000 万英镑,伦敦总部虽派人审计,却被我伪造的花旗银行存款证明蒙混过关 —— 没人愿意多走一步去核实银行账户的真实性,正如董事长彼得・巴林所言,他们本就觉得资产负债表 “没什么用”。
1995 年 1 月 17 日的阪神大地震彻底击碎了我的幻想。日经指数断崖式下跌,每跌一点,我持有的十万手头寸就蒸发两百多万美元。我开始每天向伦敦索要 1000 万英镑追加保证金,总额很快突破 1.1 亿英镑,远超英格兰银行规定的海外资金上限。2 月 24 日,当亏损达到 14 亿美元 —— 超过巴林银行全部资本储备时,我知道一切都完了。连夜逃离新加坡的我,四天后在法兰克福机场被捕,而那家见证了两个世纪金融风云的银行,在 2 月 26 日正式宣告破产。
庭审时我才知道,新加坡期货交易所早在 1 月就曾对 “88888” 账户的资金问题提出疑虑,却未得到总部重视。1995 年 11 月,我因欺诈罪被判六年半监禁,在狱中写下《我如何弄垮巴林银行》时,常常想起彼得・诺里斯的话:他们总以为员工都会 “时刻把公司利益放在心中”。1999 年保外就医后,我在伦敦的小电影院里与这位前首席执行官偶遇,屏幕上正放着根据我的故事改编的电影。那一刻我清晰地意识到,我是如何搞垮巴林银行的,从来不是一个人的疯狂,而是整个体系在信任与制度间失衡的必然结果。如今 “88888” 账户的数字早已清零,但那场由一个错误账户引发的金融悲剧,仍在警示着每个忽视风险的人。